
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5023
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5023
白花花的纸钱扔了一地,灵堂前面还插着一根招魂幡儿。 王老爷子的棺材就摆在当间,吹拉弹唱的师傅们皱着眉头,腮帮子鼓的老高。不远处还有几个和尚搁那儿念经。

 胖猴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85552
胖猴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85552
《水底葬坟》 你见过口中长眼的人吗? 你见过脸生鱼鳞的人吗? 天下疑难杂症多如牛毛,但大多都有药可医。 但唯有一种病,却非普通药物可以医治,那便是癔病。 我叫孙初七,师傅说孙悟空是我的祖先。

 六青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81710
六青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481710
怎么说呢,我能了解到清醒梦,是源于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。 清醒梦知道的人恐怕不多,简单地说,就是在梦中保持清醒的意识,所谓梦中知梦。别看人类科技这么发达,但梦究竟是什么,众说纷纭,谁也说不清楚。

 恒宸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68586
恒宸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68586
日头偏西,西边的天际出现一片红晕。 疾风吹过,满山的松柏、翠竹发出“哗哗——”、“呜呜——”的怪叫着,像是阵阵呜咽之声。 一个道士身背采药的篓子,沿着弯弯曲曲的石板路,跌跌撞撞的向山顶奔去。

 黄半仙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16584
黄半仙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16584
灵山昆仑! 一间古色古香的茅草屋中,身穿布衣的年轻人看着木桌上留下的东西,苦笑着摇了摇头。 他叫无根生,在这里修行十余载,如今正是弱冠之年。 桌上摆放着一张字条,一封红包,还有两张地契。

 归途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86905
归途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86905
深夜两点,黑到伸手不见五指,市郊三十公里外的河堤上空弥漫着血腥和腐臭的气息,警灯的光亮在天空里闪烁,划过了一道分离开了生死的警戒线。 警戒线里面的白色布底下隐约的可是看出盖着一具尸体,血腥的味道就是从这个地方传来,我接到通知的时候心也揪了起来,这已经是本月的第四起凶案了。

 金生水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19264
金生水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19264
我叫王长金,家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,祖上八代都是苦哈哈的穷酸命。 到了我这一辈,好不容易考上了高中,可因为家里穷,没办法凑够学费,只能辍学外出打工。

 混天道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00219
混天道人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00219
1920年的上海。七月的某一天,一家专载花边新闻、野史杂说、明星逸事,以此来哗众取宠的小报《明汇时报》刊登了一张类似于“海市蜃楼”的照片:一条环绕着小山的河流,在河流的上空,雾气迷漫之中,隐现一座城堡的景象。

 熙金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57141
熙金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57141
2013年9月11号。 我叫秦枫,是一名刚刚步入大学生活的一名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,入学后我才发现,大学生活和我想象的似乎并不太一样。不过,我在寝室里结识了一个高高瘦瘦,皮肤黝黑,带着近视眼镜十分幽默的男生——周江龙。

 黑石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95016
黑石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95016
我叫袁希伟,家住农村小山沟,没见过什么世面,和老爸承包了几十亩荒地种果树。 我们辛苦了三年,饱受风吹雨打,每天挥汗如流,终于等到结果的时候,就盼望今年能有个好收成。

 维京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10787
维京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310787
中国有句谚语:闰七不闰八,闰八托刀杀。 我生于公元1976年10月8日亥时,那一年为龙年,闰八月,我是第二个八月十五出生的,那天的节气为“寒露”。就在这一年,吉林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,三位伟人相继去世,当然,那一年还有死伤几十万人的唐山大地震。

 冰川雪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45773
冰川雪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45773
四月尾,初夏。 位处南方的广越市,天气已很炎热,室内开起了空调。她抿了一口冰柠茶,看看窗外。 云层不知何时厚重起来,遮住了一半太阳。太阳放肆的光芒稍微黯淡下来。

 双雄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9904
双雄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9904
我叫姚强,九零后,外号土豆,碧水市重案中队长。 碧水是座旅游小城,重案极少发生,所以日子更多时候过得都很平静。 今天(7月24日)是星期天,天气闷热,令人浑身乏力不想动弹。 我一个人在家,晚饭后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,看着看着便睡着了。

 箜铃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09339
箜铃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09339
鬼,想来大家多少都知道一点吧,不过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世界上存在鬼。过去的我也不相信鬼,可是随着渐渐的长大,世界观也慢慢的有了变化。 我认识到除了阳光灿烂的活人世界,还有着一个光怪陆离的灵异世界,当然或许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世界,它们只是没有被发现或者公之于世。

 木渎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53944
木渎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53944
位于M市的A大学是本市著名的工业大学,对于上过工业大学的人都知道,这类大学可谓是阳盛阴衰,一个招牌砸下来,砸到十个人顶多就一个女的,这还算好的,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砸到的都是男的。

 李阿公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59899
李阿公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59899
在我的家乡,流传着很多关于鬼神的传说,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,但父辈们却常常提起,而这所有的故事中,有一个给我的影响最深,因为我不止听见一个人讲,几乎所有寨子里的人都知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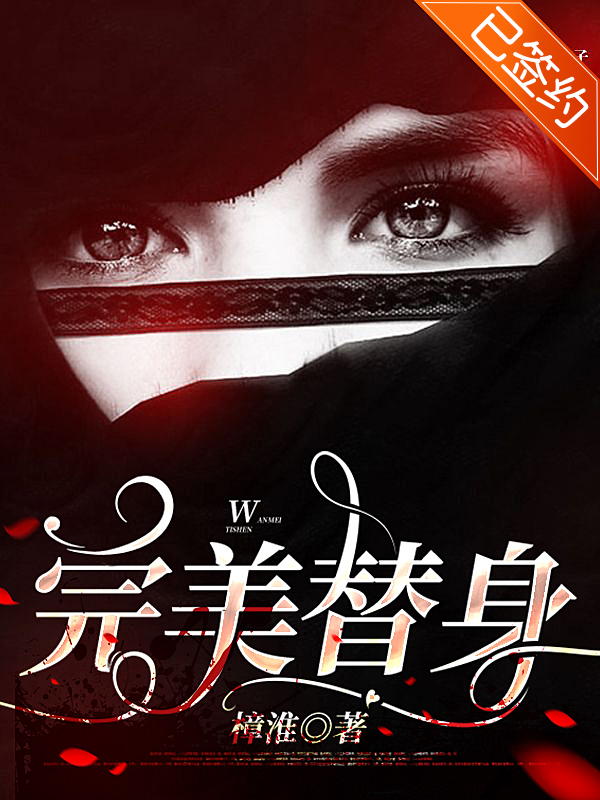
 樟淮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70594
樟淮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170594
“五陵年少金市东,银鞍白马度春风。”如果,我可以和他换一个人生就好了。 你是否,也曾这么想过? 2004年夏,中国渝州永北区新城,深夜雷鸣天,暴雨已经连续下了三天三夜了。

 紫霄道士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3087
紫霄道士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3087
寂寥的黑夜一抹红光飞啸着从遥远天际划过平静中透着诡异的大地,直插云雾迷绕的山间。 “这可怎么办是好?”一位身着朴素但眉宇之间不失大雅的中年人在院子里来回迈着步。

 满腹经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4360
满腹经纶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14360
邺城,北临漳水,南面冀山,可谓是青山绿水,颇为秀丽。近些年来,邺城发展的也很不错,特别是漳水一带,高楼耸立,漳水大桥气势恢宏,俨然成为邺城的地标建筑。

 摩登大盗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60084
摩登大盗 |
悬疑推理 |
完本 |
260084
“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,人类会使用什么武器,可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,人类使用的武器是石头和木棒。” ——爱因斯坦 未来某一天,中国四川。 三星堆博物馆的夜色娴静如水,清澈无垠的星空浸润着梦幻般的建筑群。